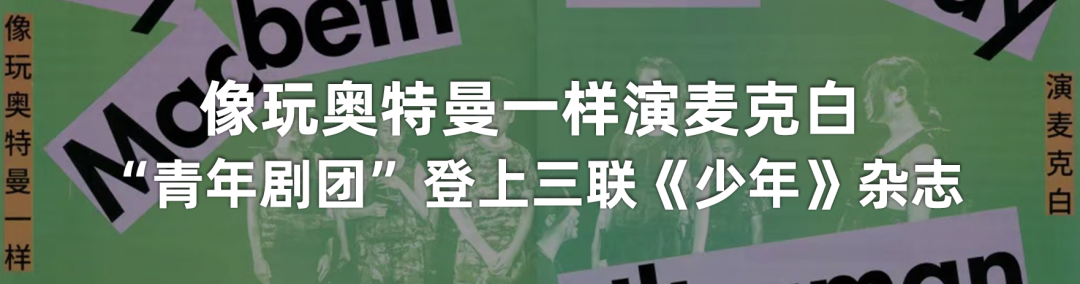它不是个人问题,是被个人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——《我们》导演采访
距离《我们(或个人问题)》上演还有一个月,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部戏剧,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采访。让我们一起听听《我们》的幕后创作故事吧!
采访: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 金燕
受访:《我们(或个人问题)》导演 曹曦
故事从何而来
金燕:我知道你们抓马剧场以前的创作是会有一个基础的故事框架,然后在框架下深入探讨,但《我们》是没有框架和大纲的,完全是孩子们自己生发出来的剧本,为什么敢冒这样的险?创作初衷是什么?
曹曦:排完《麦克白》后,我发现孩子们对日常交往的需求大于承担戏剧的责任,戏剧成了他们社交的借口。当然社交很重要,但社交和戏剧承担如果能同时发生就更好了。所以我想做一些跟他们相关性再强一点的作品。虽然《麦克白》的意义跟现在的孩子们很近,但故事本身离他们很远,我希望有一部从题材上就切入他们生活的作品。
金燕:完全由孩子们自己创编,有很大不确定性。在《我们》成型之前,你不会担心么?这个戏是怎么创编出来的?
曹曦:编创肯定是有难度、有风险的,所以排演过程是起起伏伏的。创编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些练习,比如说我们做了表情包的练习,让孩子去研究社会新闻,写日记。手机已经成为很重要的物件了,那我们就做很多关于手机的练习,这些有时看似是生活中的纷扰的东西,在戏剧里被有意识的使用了,于是它的优势和劣势也能被意识到。这个戏里有一整场是用手机表演的。
金燕:这些都是元素,但如何形成一个故事呢?
曹曦:做这些练习的目的是,我们要用这些元素虚构一个世界。比如虚拟一个16岁的小孩在网络上的遭遇。我给一个起点,这往往是一个事件集中爆发的点,然后大家去讨论这个事件发生的过程,以及过程中一个个小的事件。网红这个事情讨论了几周,我会给他们设置一些问题,比如网红从老家来带了什么物件,第一个100位粉丝见面时是什么物件,去美国巡演时是什么物件,然后这些物件怎么来的,你要根据物件来创造动作,在动作基础上生发出场面。慢慢地就形成了有情节、有张力、有人物、有动作、有意义的戏剧段落。
我的任务是,当这些进程不是特别顺利的时候,我要来给予一些刺激,一些其他的情节,比如说,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中有一个泼墨的情节,这个事件是我带来的,至于他们怎么理解这个事件怎么建构这个事件,是他们自己的事儿。
金燕:网红、手机……听起来与现实生活好近,这是孩子们自己想要的方向吗?
曹曦:去年十月,要做下一个戏的基本计划的时候,我把青年剧团叫在一起,问他们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戏?他们说了:首先,不要家庭纠葛戏,要有音乐元素的,要搞笑的,不演成年人……这些是我的限制。当然讲述青少年的故事不可能一点家庭纠葛都不涉及,但肯定不像《隐形的我》那种大面积地描述家庭了。
然后我给他们看了一些英剧美剧的一些素材,让他们理解喜剧不一定是搞笑,喜剧跟创作悲剧是一模一样的。
所以,孩子会自己提出一个想法,这个想法往往和她自我的感受以及别人如何看待她有关,比如排家庭纠葛的戏很痛苦,演成年人很尴尬……想要避免这些感受才是他们背后的意图;特别是青春期阶段的一些社会化方面的担忧。喜欢搞笑,也是因为它很安全不是么?我们的文化总是喜欢搞笑,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权力决定更多的事情,于是人很容易变得愤世嫉俗,笑是一种对抗这个的方式。年轻人特别害怕“社死”。剧团的两个小孩最近参与了一本书的创作,在一次采访中,她们就特别担忧在豆瓣上有人评论他们,说不好的话,那么这种想法是怎么来的?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?任何人,当建立一个所谓的素材或者方向,其实都要去想想它背后的渴望、需求是什么。成年人也一样。
孩子们的担忧从何而来?
▽一键直达采访《我屏蔽了所有成年人》▽
现实中的“个人问题”
金燕:据说这部戏与校园暴力网络暴力有关,你们怎么想到要做这样一个刺激的故事?
曹曦:其实并非我们想要讲一个暴力的故事。我们只是想讲年轻人生活的故事,暴力是这个生活中的一个侧面。它既不是完整的年轻人的生活——我们也不寻求完整及客观;也不是照搬生活。而是孩子们希望通过这个戏提出的问题。上周我和孩子一起创建结尾,我提出很多人可能想从这个戏的结尾看到一点希望。一个孩子说,他们需要的是思考,不是希望。我挺骄傲的,觉得孩子们其实比我们明白很多成年人的游戏并没有什么用。 之前我让孩子们创作一个视频,有一个孩子说我这有一个视频特好玩,然后就把他同学割腕的视频转过来。现在的和以前不一样,以前这些痛苦挣扎矛盾都有,但大体上是你个人的事儿,是周围小圈子的事儿。现在这些视频本人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微信里转了这些东西。这些视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一种宣泄的作用。影像会给你一种十分真实的感受,所以你不需要写什么虚构的影视剧了,上微博比电影好看多了,而且还会跟随,一会儿这事儿反转了,跟电视剧是一样起伏跌宕,但同时又是现实,这会带来极大的快感。你看影视剧里的割腕,和你同学转给你他认识的谁谁谁割腕,那个刺激是不一样的,影视剧利用虚拟来尽可能接近现实,但这个就是现实。我在替你流血,要么是你不敢的,要么是你想做没有条件的,我在为你制造这种影像这种记忆……这些是他们特别关注的。那么49中的学生坠楼事件出来之后,就有个主线了。 我们的社会的确变得越来越暴力了,而且暴力的呈现方式也越来越隐秘。其实今天你已经很难在街上看见有小流氓在打架,但微信群里很多,用视频打架,用文字打架,用隐晦的暗语攻击别人。年轻人生活在这么多层次的现实空间里,特别又遇到青春期身体激素发展不稳定的期间,对这些东西还是很敏感的。
金燕:剧名为什么叫《我们(或个人问题)》?有点拗口。
曹曦:故事成型的时候正巧发生了49中学生坠楼事件,这种事很普遍,孩子们也很关注。那个事件后官方报道中写到:“该生因个人问题轻生”,那这个“个人问题”是什么?每一幕孩子们都创作一个虚构的场面来描述这个“个人问题”,表达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表述。
比如你看到的段落,一个小孩在操场上跑步摔倒了,害全班陪着跑三圈,她就遭到了集体的围攻,她通过给全班买饮料来赔罪。为什么是发红包或者买饮料?你不能理解为“小孩嘛,开玩笑”。在办公室,谁帮了谁忙,你会开玩笑说:“给买一杯双响炮。”为什么不是买两本书,而是双响炮?这些玩笑背后都有政治。所以她不是个人问题,是被个人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。社会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的,只是大家意识不到。所以小朋友主动提出我给大家买什么,是因为她觉得社会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。
另外我认为,成年人权力不够,青少年就会痛苦。我们听到很多家庭矛盾时会有这样的台词:“我上班已经这么累了,你怎么还给我捣这么多乱?”为什么孩子会觉得痛苦?孩子会觉得我跟你之间我优先的吧,我为什么要理解你上班辛苦这件事?难道不是应该你的伴侣、同事、亲友、领导、社会、法律、权威、公共媒体、舆论来理解你吗?为什么要我一个没有独自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来理解你?社会对成人的关照不够,成年人没有权力,就会让孩子感到痛苦。你说这是社会问题还是个人问题?
▽点击下方的海报▽
了解《我们》的剧情故事
音乐创作
金燕:我看过《我们》的排练,孩子们自己的现场乐队在演奏,感觉很激情,想知道和以前的少年剧场青年剧团的创作过程有什么不同?
曹曦:我个人认为,在一台演出中,你没有必要获得所有的满足,很多人喜欢戏剧因为戏剧是综合艺术,不是,别的也可以是综合艺术。戏剧有自己的一套逻辑,它只能解决它能解决的一小部分。
音乐像戏剧一样,是有自己独特的逻辑的。它需要你去了解如何在戏剧中使用它,而不是关注它给你带来的感官的感受。
金燕:音乐都是孩子们自己创作的吗?你怎么指导他们创作的?
曹曦:好多孩子都会乐器,都学了好几年,有的孩子拉琴拉得很好,他能拉勃拉姆斯,能弹贝多芬,但无法即兴,无法创作。我不需要你技术有多炫,不是给你一个谱子你回家练,我需要你能用音乐来表达,你得理解这场戏是讲什么的,它应该是什么情绪,然后再创作一个跟气氛相关的音乐。这个不难,但又是个综合能力,不是每个人都有。
实验?还是日常?
金燕:这算是实验戏剧吗?
曹曦:做艺术哪个不是实验的?在我眼里艺术都是在不停地实验、不停地创新,但如果只是形式上变得花哨一点,没有思想上的颠覆性创造,这不算什么实验艺术。我不接受被当作实验艺术,我只是认为这是戏剧,戏剧有很多种,这只是其中一种而已。形式上没什么新鲜的,直播啊手机啊都没什么新鲜的,我关注的是不是形式,而是形式和内容的嫁接。 我们在戏里大量使用视频,主要还是考量戏剧的内容——这个隐秘的、手机里的世界,可能通过视频展现是更好的方式。 有些人也许认为将一群年轻人放在舞台上,感觉很实验。有时,孩子们在街上采访,为了创作视频,获得的回应几乎都是——你们怎么不上学?上学不是一个14岁青年的全部。她们有自己的生活,想法,意识和权利。我们的社会特别不适应看到一个14岁的孩子在非学习的环境中。我希望“双减”之后,能在公共空间更多的看见孩子的影子。十四五岁的他们应该出现在街角、剧院、法庭、音乐厅、社区、美术馆里,用她们更加敏锐——而非纯真的眼睛,发现这个世界的不公,并且将它讲述出来。
▽了解青年剧团的往期故事▽
来吧!
直面鸿沟青年剧团
《我们(或个人问题)》
扫码购票
▽

演出时间
▽
2022年1月23日(周日)
10:30 / 14:30 / 19:30
【温馨提示】
本演出适合
10岁以上孩子及成人
来见证我们
对“我们”的探索!

2018年5月27日—28日,“2018中国民办教育领袖峰会”在北京隆重举办。

抓马宝贝应邀参加第二届全国戏剧与教育应用大会系列报道 2017年5月19-21日,抓马宝贝应邀参加第二届全国戏剧与教育应用大会。本次大会由中

英国教育戏剧大师Dr. David Davis莅临抓马宝贝参观交流! 2017年5月18日,英国教育戏剧大师大卫·戴维斯(Dr. David